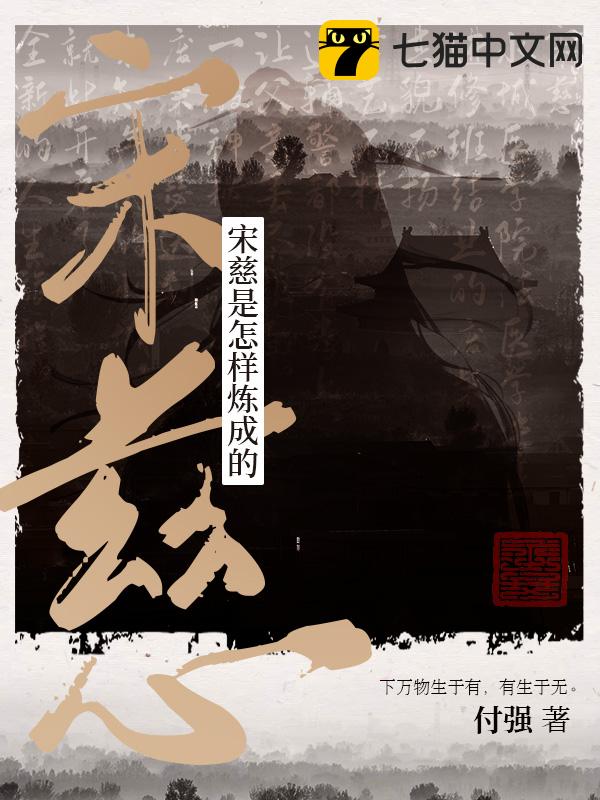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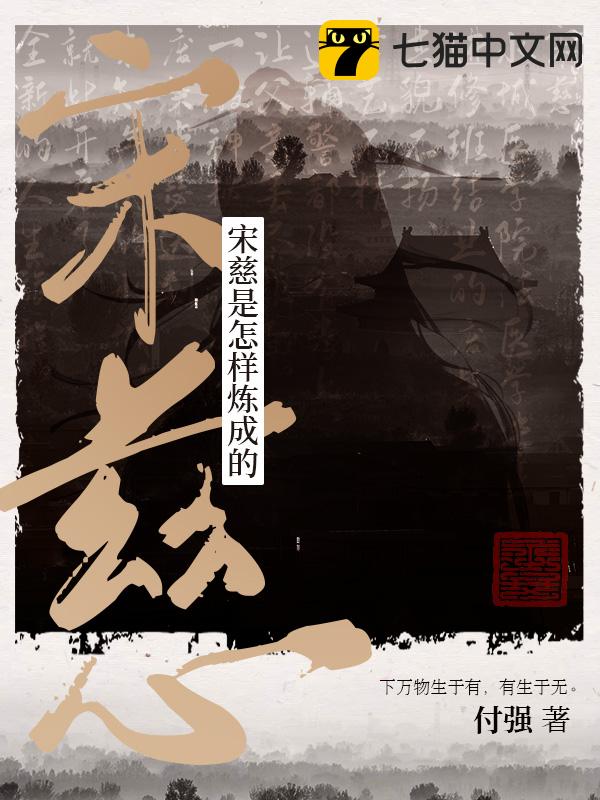
飞身扑向嫌疑人那一刻,年轻辅警孱弱的身躯弯成一张硬弓。
耳畔掠过水城峡谷腥湿的海风,他像狩猎的鹰隼那样从天而降,高举警棍,务求一击必中。
宛如定格了一般,身强体壮、头大如斗的重案在逃嫌疑人愣在当场,因惊诧而微张的瞳孔映射出这名年轻辅警的飒爽英姿。
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父亲以及同事眼里的废柴、卢瑟,宋慈真的豁出去了。
A级通缉令、重案在逃嫌疑人、立功受奖……
这些特别的字眼让这位宁安路派出所的年轻辅警肾上腺素飙升,抓捕过程中不顾带队探长的一再告诫,擅自脱离搜山阵型,凭直觉包抄,终于抢先发现了逃犯藏身处。
树林里影影绰绰,多名警局探员正朝这边围拢过来。
前有峡谷,后有追兵,嫌疑人无路可逃。宋慈见状大喜,立功心切的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呼叫增援,而是抢先向这名罪孽深重的逃犯发起致命一击。
这是证明自己的宝贵机会,怎么可能轻易放过?
手起棍落,嫌疑人抱头哀嚎,增援警力随后到场,将逃犯拘捕。从今往后,自己将不再低人一等,不仅能在辅警队伍里抬起头来,更让望子成龙的局长父亲刮目相看。
警棍在空中划出一条完美的弧线,狠狠砸向嫌疑人的脑袋。
宋慈似乎看到了预想中自己“只身擒凶”的英雄一幕,冷峻的表情中藏着几分得意,心说上了公安部A级通缉令的重大在逃嫌疑人也不过如此,并不比其他人多长三头六臂……
这一闪念尚未结束,他便意识到有些不对劲。
嫌疑人近在咫尺,此时宋慈可以清楚地看到,对方怪异的眼神并非惊诧,更像是讥笑、嘲讽他的自不量力。
心里咯噔一下,但是后悔已经太晚了。
身高马大的嫌疑人不躲不闪,待宋慈飞扑过来的瞬间,突然出手掐住他的脖子。
双脚悬空,徒劳挣扎,就像被对方拎着的小鸡崽儿。
粗壮得宛如大型起重机械的臂膀开始徐徐移动,宋慈惊恐地发现自己被移到了峡谷这边,脚下便是万丈深渊。
头冒冷汗,四肢瘫软,连告饶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难道自己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亡命徒终结吗?虽然极度不甘心,但是在绝对力量面前终究无可奈何。
嫌疑人恶狠狠地盯着他,慢慢松开了手。
宋慈的身体极速坠落,耳畔掠过呼呼的风声。不知道自己摔死之后能否被组织评定为烈士;身为警察局长的父亲再也不能逼儿子报考公务员;水城医学院法医学专业进修班的结业证书还没来得及领取;上季度的房租还有那些信用卡欠款也不用偿还了吧?
高空高速坠落让他的耳膜承受了太大压力,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。
……
乌云滚滚,遮天蔽日。水城密集毗邻的牌楼街坊在斑驳光影映射下透着一股诡异的气氛。
僻静甬道内,遍体鳞伤的死囚韩渊枷锁束手,白布囚服鲜血殷红,他已无力挣扎,唯有喉咙里发出困兽般的低吼。几名身着古代官服的狱卒将其高举过顶。一行人快步穿行甬道,裹挟起阵阵血腥。
飞檐斗拱的古代建筑群,红墙绿瓦的官府衙门,这里是未知年代的大理寺行刑处。
抱着扁担靠在墙角打瞌睡的宋慈迷迷糊糊睁开眼睛,正巧看到狱卒从眼前经过,于是好奇地探头张望。跟宋慈并肩坐在一起的是位身着麻布衣的古装青年,眼疾手快,一把将他拉了回来。
“宋兄可看清楚啦?这名死囚便是韩渊韩大人,你我按计划行事,切勿鲁莽。”
说着,麻衣青年悄悄将一把匕首塞到宋慈手里,率先挑起水桶跟了上去。
宋慈一时回不过味来,懵懂地四下张望,紧张判断着形势。麻衣青年见他站在原地,焦急地摆手示意。
将匕首藏进袖管,匆匆挑起自己的水桶走过去。
宋慈怀疑自己误入电视剧片场,难不成还当上了剧组的群演?
“哎,哥们儿,你们这是拍戏呢?”
麻衣青年停下脚步,低声叮嘱道:“宋兄莫非怀有心事?城主赵扩厚德而孱弱,朝野各派牛头马面,人鬼不分。你我今日义举便是为了国家社稷,切记奸臣不除,后患无穷!”
宋慈一乐,“词儿还挺熟。认识一下?我叫宋慈,兄弟怎么称呼?”
麻衣青年像看怪物一样盯着他,无奈地摇摇头。
跟在麻衣青年身后来到大理寺行刑处宽敞的院落。只见左侧摆放巨型镬鼎一只,锅下柴堆熊熊燃烧,现场热气蒸腾。
杂役们绢巾捂口鼻,正用特制工具从镬鼎内捞取尸骨。
冒着热气的骷髅头被装进殓尸袋。
院落中央布设巨大的绞刑架,有杂役正将吊在绞架上的尸首卸下来。院落右侧设置一处行刑台,木板铺装,离地三尺。
行刑台上的刽子手手起刀落。
鲜血四溅,犯人登时身首异处。
即便猜测是在片场拍戏,宋慈亲眼目睹这血腥一幕依然感到阵阵恶心,频频干呕。
“我X,这也太逼真了吧?!”
麻衣青年低声提醒道:“宋兄,公案后满脸横肉者便是大理寺卿杨元贵!”
宋慈扭头望去,看向不远处的公案桌——
坐在桌后的杨元贵头也不抬,提笔在一份公文袋上画个红叉,公文袋随手扔在地上……
划过红叉的公文袋已累积厚厚一堆。
行刑台这边的杂役们分工协作,有人麻利地收拾犯人尸首,有人水桶冲洗行刑台血迹,动作娴熟,绝不拖泥带水,事毕迅速撤离。
宋慈和麻衣青年挑着水桶走了过去,与杂役交接。
扑通一声,枷锁傍身的韩渊被狱卒们重重地扔在公案桌前。
杨元贵见状不禁皱起眉头,起身来到他的面前,伸手刚要搀扶,忽然想到对方死囚身份,只能驻足观望,心疼打量。
韩渊虚弱异常,但紧咬牙关,拳头微握。
杨元贵恨铁不成钢,哆哆嗦嗦地指着韩渊,痛苦地摇摇头。
“韩大人啊韩大人,你我同朝为官几十载,没想到你居然是祸国殃民的奸佞小人!勾结韩党余孽,鼓噪煽动、阴谋造反,你们这些人……真是有负城主皇恩啊!”
韩渊苦笑道:“韩党?仅仅缘由韩某姓氏,便捕风捉影怀疑我与韩党余孽有关联?狗屁关联!欲加之罪何患无辞!”
杨元贵理解地点点头,转身回到公案桌后,接过评事谭登递来的公文袋,打开卷宗沉痛宣读。
“经刑部核准,广东经略安抚使韩渊结党谋反罪行成立,依大城刑律严惩,判,烹刑!”
读毕,杨元贵捶案顿足,潸然泪下。
韩渊吃惊地望着他,急忙扭头看向院内镬鼎——
杂役们已开始向锅下柴堆泼洒油料,大火熊熊燃烧,鼎内沸水翻滚,热气升腾。
韩渊气得浑身发抖,突然呕吐不止,污秽满地。
“真是好演员啊!演得太像了。”
看到这样精湛逼真的演技,宋慈不禁发出由衷赞叹,差点儿鼓掌叫好,转向麻衣青年又问道:“哎,哥们儿,我们两个待会儿演什么?怀揣利刃,不会是荆轲刺秦王的戏份吧?”
麻衣青年望着杨元贵恨得咬牙切齿,眼睛湿润了。
“想必雎大人正火速赶来,你我不可轻举妄动!”
一名杂役来到宋慈、麻衣青年面前,粗声粗气地命令道:“宋慈,九条,又想偷奸耍滑不成?还不赶紧再挑水来?!”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