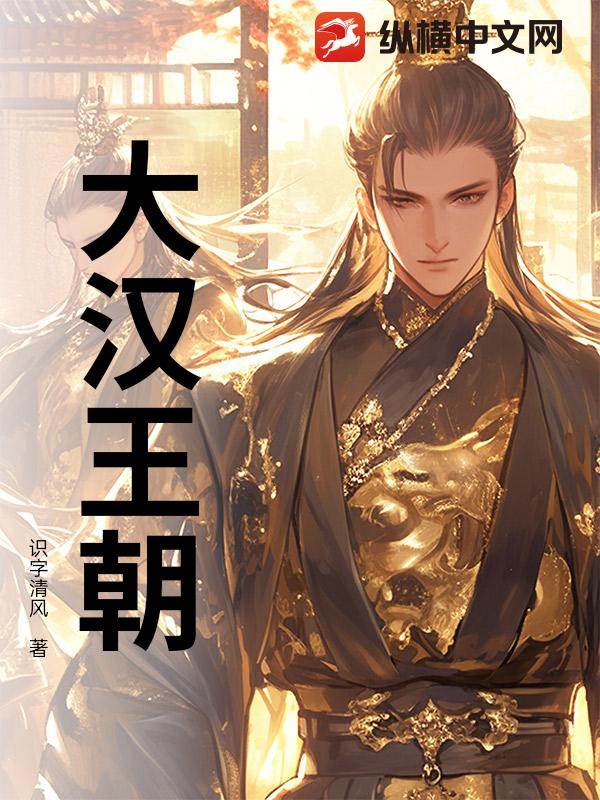### 世界观设定
- **时间背景**:1950年冬至,志愿军第九兵团秘密入朝初期,长津湖战役前夜
- **地理环境**:朝鲜北部狼林山脉腹地,零下40℃极寒雪原,冰封的盖马高原
- **历史背景**:志愿军昼伏夜行躲避美军侦察,补给线被炸断,单衣薄裤对抗钢铁洪流
陈江河的睫毛结了层白霜。
他趴在雪窝里,能清晰听见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。单薄的棉衣早已被寒风浸透,每片雪花都像钢针般扎进骨髓。右手指节泛着不正常的青紫,却仍死死扣着那支莫辛纳甘步枪。
"小陈,把脚趾头动动。"身旁传来沙哑的山东口音。赵铁柱往掌心哈着热气,黢黑的脸被冻出大片紫斑,"这鬼地方,撒泡尿都能冻成冰溜子。"
陈江河试着蜷缩脚趾,却发现双腿早已失去知觉。三天前从临江跨过鸭绿江时,他还能看见江面上未融尽的枫叶,现在整个世界只剩刺眼的白。第九兵团十五万人昼伏夜行,在美军侦察机的眼皮底下翻越海拔两千米的狼林山脉,单衣薄裤对抗零下四十度的严寒。
"轰!"
西南方突然腾起火光。陈江河看见无数曳光弹划破夜幕,照明弹将雪地照得惨白。美军F4U海盗式战斗机呼啸着俯冲而下,机翼下的凝固汽油弹像恶魔之卵坠落。
"卧倒!"
赵铁柱猛地将他扑进弹坑。灼热气浪掀飞积雪,陈江河的耳膜嗡嗡作响。他闻到皮肉烧焦的味道,转头看见三连的通讯员小王在火海中翻滚——那个爱唱评剧的天津小伙,昨天还偷偷往他兜里塞了半块高粱饼。
"医护兵!"陈江河刚要起身,却被铁钳般的手掌按回地面。
"别动!"赵铁柱的眼白布满血丝,"是燃烧弹,救不了了。"
雪地上腾起数十道火柱。陈江河看见有人抱着燃烧的战友在雪地里打滚,看见卫生员林秀云撕开急救包,用绷带蘸雪水往伤员伤口上敷。她的棉军帽不知何时掉了,齐耳短发在热浪中翻卷,像面倔强的战旗。
"喀秋莎!是咱们的火箭炮!"不知谁喊了一声。
东面山脊突然亮起流星般的尾焰。陈江河数到第十二道火光时,古土里美军阵地腾起连绵爆炸。他听见赵铁柱拉动马克沁重机枪的枪栓,金属撞击声在寒风中格外清脆。
"准备冲锋!"连长的声音撕开裂帛,"三三制散开!爆破组跟我上!"
陈江河吐出嘴里的雪渣。他想起跨江那夜,兵团文工团在江边唱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。月光下,十万将士的绑腿带起冰碴,像条沉默的钢铁洪流。此刻他的子弹袋里,还躺着母亲求来的平安符——绸布上绣着"精忠报国",针脚里渗着黄浦江的潮气。
"杀!"
山呼海啸般的呐喊震落松枝积雪。陈江河跃出掩体时,看见赵铁柱的机枪喷出火舌,弹壳在雪地上烫出焦黑的圆点。美军阵地的探照灯扫来,他本能地翻滚躲避,却听见身后传来闷哼。
"老赵!"
机枪哑了。陈江河爬回掩体,发现赵铁柱的棉衣右襟渗出血花。山东汉子咧开干裂的嘴唇,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:"给...给秀云同志...这是...俺的党费..."
纸包里是五发保存完好的机枪子弹,弹壳上用刺刀刻着歪扭的字迹:解放台湾。